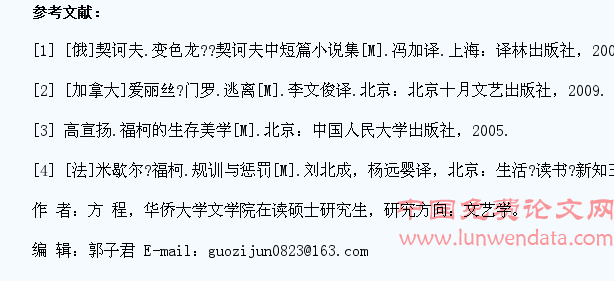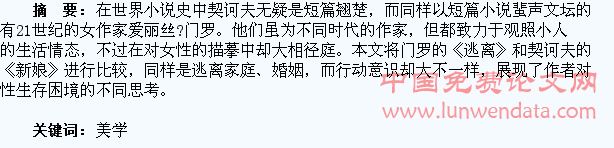
门罗的《逃离》和契诃夫的《新娘》是两部关于女人存活处境的简短小说。《逃离》讲述了主人公卡拉因不堪忍受老公暴力的对待而逃离,但最后又苦涩地回到原点的故事。《新娘》则是关于一位马上出嫁的贵族小姐娜佳,在别人的鼓励和内心的召唤下逃离了平庸生活的故事。这两部小说的中心轴都是“逃离”,不一样的是卡拉被生活弹回来了,而娜佳却与过去彻底割裂。在对女人存活困境的考量中,门罗有一种悲剧意识,女人没办法学会和拯救自己,在生活复杂的缠绕中,她看到了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无奈和意欲挣脱但又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痛苦。而契诃夫则极具批判性,大肆挞伐游手好闲无所追求的平庸生活,急声唤醒女人的自我意识对生活进行革命。虽则这样,但在二者的小说中,仍能感觉到他们性别差异中的一同情感指向――对女人存活的终极关怀,尽管这种同一性中又分驰着两种态度,但最后会在拥抱人性的冷暖中汇合。
1、存活困境:理性启蒙与现实秩序的冲突
“逃离”一直都是作为文学母题被作家们进行异质书写,各种形式的“逃离”一直在面临存活困境的威胁下谋划行动的。当现有些生活秩序在价值欲望的审判下变得扭曲时,逃离就成了大家对现实刺痛的适合回话。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面临着对现实生活的困惑,这种困惑来自于身处边缘控制而又没办法准确地把脉我们的生活。《逃离》的女主人公卡拉,在老公的多次伤害下最后爆发,逃离了她过去迷恋的老公,和被现实笞挞地面目全非的生活。在卡拉的婚姻里,老公主宰着她的所有,这非常符合男权社会里女人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模式。卡拉的自我意识长期处于被压抑被控制的状况,当她每一次发源于我的声音时,都会被男权更大的声音覆盖。因此,卡拉一直是作为被规训的对象而存在,老公每一次的权力运作都是对卡拉恶狠狠的踩踏,所以逃离也就势在必行。而在《新娘》中,虽然无明显的男权操控痕迹,但社会环境、风俗观念、价值取向无一不渗透着男权思想。主人公娜佳此生的目的就是出嫁,这种观念在19世纪的俄国社会比比皆是,娜佳的妈妈、祖母等都是那个年代女人生活状况的投射,她们围绕着嫁人、生养孩子来度过一生。男士的私有财产,社会的助产者……这一系列标签式的存在让大家看到了女人对自己价值认知的匮乏。男权把女人囚禁在婚姻家庭中,让她们误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从而在日积月累的损耗中磨灭她们的女人意识和行动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卡拉和娜佳都感觉到了现有秩序的不合理性,因此觉醒的种子在心中悄然扎根。卡拉的觉醒,一方面是对委顿的生活的反抗,其次是理性意识的萌发,两者经纬交织成卡拉的挣扎过程。作为女人,她被剥夺了拥有自我意识的权利,对现有生活秩序感到愤懑后,卡拉的哭诉是觉醒的象征,在本能冲动的驱使和邻居的帮忙下她选择逃离,但逃离了现有些婚姻生活后,她又陷入了前途未卜的恐慌和无根的漂泊感中。想要逃离生活的深渊,却发现上岸后又有新的黑暗需要克服,这种悲哀也是海量底层而渺小的女人都面临的困境。
契诃夫《新娘》中的娜佳虽然衣食无匮,但仍然摆脱不了这种命。高高在上的娜佳天天什么事都不干,只醉心于无聊的贵族社交活动,生来就置身其中的娜佳并未意识到其中的罪恶,只不过隐约有的质疑的念头。直到好友萨沙对她耳提面命地进行了劝说,她才郑重地对现有生活进行了考虑。萨沙唤醒了她的觉醒意识,让她对我们的不安得到了确认和引导,因此一种想要和平庸生活决裂的想法应运而生。最后娜佳践行了她对自己的追求,完成了重建自己人格的转变。虽然她对将来也有担虑,但面对废墟一样的过去她选择了义无反顾地奔赴神秘莫测的以后。
在理性意识的觉醒和现实秩序的冲撞中,卡拉一路跌跌撞撞充满挫败感,理性意识的缺席让她没能逃出生活的怪圈。相比娜佳要幸运不少,她可以在认识到现实后飞速地做出反应,听从内心的召唤,因而在突破传统的创造活动中获得了新生。两人的逃离都是对这种存活困境的本能抗争,但一个用理性启蒙撬开了现实生活秩序的罅隙,一个仍在裂缝中艰难地前进。
2、同途殊归:悲剧意识与批判意识的碰撞
两位女人都想试图颠覆二元对立的主客体模式,摆脱男权的控制,渴望消解主体性,消解作为他者的存在,试图发现生命的可能性和自由。无论是门罗还是契诃夫,他们都注意到了社会生活的监禁模式,卡拉生活在老公的监视下,他无视卡拉的人格,戳伤她的心灵,并且限制她的交往自由;而娜佳则被家庭的体制观念规训,将她拴在没爱情的婚姻和庸碌的家庭日常,抹杀了对自己人格的构建。这种无所不在的控制就是女人存活困境的无奈和痛苦。
但在这种近似于恶的痛苦中,娜佳通过逃离成功地解放了自己,同传统彻底决裂。而卡拉因自己的局限性半途而废,逃离没能让她获得救赎,反而囚禁了我们的真实欲望,限制了生命的可能性。同样的行动,不同的结果,不只体现了阶层的差异性,也外化了两位作家异质的生活观。
非常显然,门罗的《逃离》中带有命定的宿命感和深沉的悲剧意识。她关注女人的生活细节,更洞烛细节背后的复杂情绪和生活体验。卡拉是一个胆汁质型的人,她未曾理性地思忖过生活,所有行为都是冲动使然。首次逃离爸爸妈妈是由于厌倦和性迷恋,意欲追求更真实的生活。但结婚以后才意识到更真实的生活只是年轻时不切实质的幻想罢了。沉重繁琐的婚姻生活越来越还原了老公自私冷漠的本质,不堪重负的她选择了第二次逃离,但最后还是在强硬的现实面前折戟。她很难面对逃离衍生而来的恐惧,生活的磨难早已透支了她的精气和意志,弱化了她的自主行动能力。她的存活状况只不过一种对绝望的耐受,她的反抗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无目的性,因此注定失败。物质基础惨淡、精神意志松懈、对自我没认识规划,每一次的离开与其说是逃离不如说是逃避日常很难调和的矛盾,何况她还行动延宕。所以最后回到当初离开的地方,再一次成为规训的对象也是势必。生活的可抗力和不可抗力在卡拉的逃离中拉扯着她,她没能对生活的质疑进行转化和创造,因而没办法重建自己也没办法真正达成逃离,只能靠压抑和断绝魅惑来寻求现世安稳。 但娜佳的逃离充满了彻底性,她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充满了惊声尖叫。在萨沙的导引下,她意识到了错误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一种秩序,以至于大家不可以发现这种错误。但生活就意味着擅长犯了错误误以便进步。在外出求学的过程中,她嗅到了身后世界的靡腐之气,看到故乡游手好闲的亲人毫无罪恶感地继续过着让人嗤鄙的生活时,她坚定了我们的想法,也确凿了逃离的意义。而这个时候过去鼓励她的萨沙则在病中失去了以往的前瞻性,消退了对生活积极追求的矍铄精神,朽败之气同样也在羸弱的萨沙身上泛起,最后松手人寰。萨沙的死亡给了娜佳更多的力量而非感伤,这种力量来自于对平庸生活的恶心,对自己人格构建的期望,对存活意义的终极追求。逃离唤醒了她的女人主体意识,让她拥有了生命的尊严。娜佳的逃离充满了批判意识,她批判自己,批判既定的所有,对自己也有着了解的认识,信念笃定。而卡拉的逃离则布满了悲哀,她想要挣脱生活的软禁,但又因没目的而无处可逃。卡拉的存活困境是我们的冲动导致的,而娜佳的存活困境是环境形成的,两人都本能性地选择逃离,但同途殊归,彰显了两位作家对女人存活的关怀和取向。
3、终极关怀:拯救自己
日常最大的“恶”就是痛苦,来自于求不能。无论是卡拉还是娜佳,她们都否定了现有些生活秩序,想要追寻心之所向的新生活。但卡拉的信念没娜佳那样强烈,虽然她意识到了自己身处的威胁,但她没进行关于“自己文化”的考虑,缺少明确的指向,所以行动充满了障碍和延宕,乃至后来处境越发艰难。而娜佳的存活态度非常坚决,她在厌恶平庸的生活后选择了另一种有意义可循的生活,这从侧面来讲是基于她对自己的相应认识,与卡拉的不知所措完全不同。同样是具备救赎的想法,娜佳在思想上的考量比卡拉要清醒得多,因而娜佳考虑的对象最后可以得到澄清和确认,而卡拉只能继续浑噩地生活下去。这也就是作为像卡拉一样的女人悲哀的地方,她们对生活意义的迷茫、对自己的认识缺席酿就了这种悲剧形态。
契诃夫和门罗对女人的存活困境的斟酌、拿捏和考虑都很精确深刻,他们将生活中的二元对立困境呈目前人物眼前,虽然一个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宿命悲剧意识,一个充满着强力反抗的批判情绪,但都践行着存活美学的基本原则,践行着对女人生命权力的捍卫和规复。